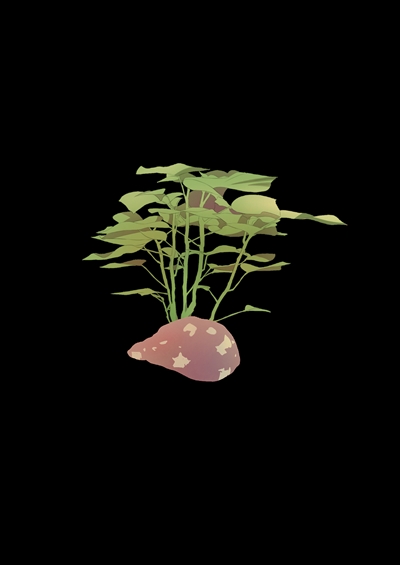□徐新
无论再怎么不舍,日子依然像流水一样逝去。似水的年华再也追不回,但遥远的往事常常在时空的隧道里悄悄闪现。纵然远离故乡,但丝丝缕缕醉人的薯香常在我的内心深处飘荡,时不时侵袭着虚掩岁月的门扉,回味悠长,历久弥香。
20世纪70年代,农村过得是瓜菜半年粮的日子,而红薯则成了我们的主食,整个冬天,家家户户吃的几乎都是红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帮助大家渡过了重重难关,可以说是我们的患难之交。
红薯生命力极强,比种植水稻实惠,所以生产队里总是挤出相当面积的土地来种红薯。
过了惊蛰,勤劳的农民便选择品质最好的红薯,埋在土质肥沃、松软的地里,用塑料薄膜盖起来,并铺上秸秆或草帘。用不了多久,嫩绿的秧苗便破土而出,清明前后把这些秧苗移栽到拢起田埂的田地里,以后只需翻几遍红薯秧,清除杂草,就等秋后挖红薯了。
每每到了秋高气爽的季节,蓝天上飘着朵朵白云,原野里红薯枝叶蔓延,成了翡翠般的绿色地毯时,人们已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纷纷走进红薯地,轻轻拉开藤蔓、扒开泥土,当看到那些红薯已经长得像胖娃娃似的,人们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
挖完红薯,生产队就根据人头进行分配,仓库前空旷的场地顿时热闹起来,家家户户的大人孩子会全体出动,板车装、肩挑、筐抬,纷纷往家搬运。当时我家穷,没有板车,父亲又在外地工作,一大堆红薯全由母亲一人用两个箩筐一趟趟地挑回去。当我懂事后,不忍心看母亲一个人劳累,就用一根小扁担,配上两个小竹篮子装上红薯,摇摇晃晃地往家里运。
红薯是经不住寒冷的,因此,在留下足够过冬吃的红薯外,其余的必须储存到地窖里。母亲挑拣那些完好无损的红薯小心翼翼地放进地窖,并在上面铺上干草、盖上泥土,防止雨雪侵袭,让它们温暖安静地睡一冬天。待留存的红薯吃完了,装到地窖里才被陆陆续续拿出来食用。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晾晒红薯干,因为它是大人小孩冬天里高级的零嘴。制作时先把红薯烀熟,去皮切成薄片,然后晾晒风干。晒干了的红薯干,像一片片翘起的树叶,很可爱。为了使之柔软甜蜜,就把它装在坛罐中,在阴凉处捂着,不长时间,红薯干的表面就会出现一层白白的粉末——白霜,那是红薯干分解出的一层糖霜,甜甜的。我们放学回家,常常已是饥肠辘辘了,抓一把红薯干,颇为心满意足。
童年时最常吃的是红薯粥。冬天的早晨,北风呼呼,我们躲在被窝里不愿起来。而母亲早就起床把红薯削掉皮、切成块,和玉米面一起放进锅里熬。熬好了糊糊,她才催促着让我们起床。纯粹的玉米糊糊是难以下咽的,但是放入了红薯后,又热又甜的糊糊居然成了美食。每次喝完,我总要把碗舔干净才肯放下。就这样,冬天的早晨永远是母亲煮好的红薯玉米糊糊散发出来的香味伴随着我们起床。现在想来,依然觉得那么温馨。
烤红薯的美味是让我最难忘的。每每做完晚饭,母亲像变戏法似的在闪烁着火光的灰烬里掏出几个红薯。轻轻吹去上面的灰尘,拿在手中拍几下,松了的皮就自动脱落,露出烤得金黄的外壳,一口咬在嘴里,脆而香甜,里面软软滑滑,甜滋滋的味道直透五脏,心中甚为舒爽。
如今远离了那片养育我的土地,每每上街闻到沁人心脾的烤红薯香味,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悄然远逝却又记忆犹新的童年时光,心底不断涌动起股股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