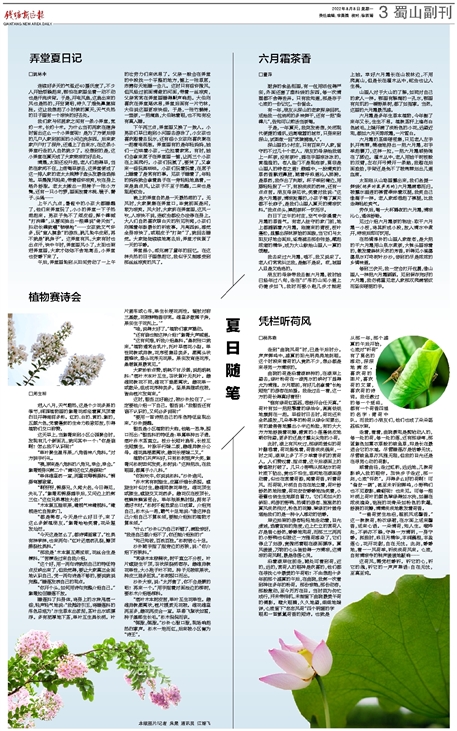□董萍
厨房的食品柜里,有一包用纸包得严实,外面还套了塑料袋的东西,每一次清理都不舍得丢弃。只有我知道,那是存于心底的一份记忆,一份留念。
有一年,朋友从深山的老家探亲回杭,送给我一包消闲的多味笋干,还有一把“柴棒儿”,告知可以煎汤当茶喝。
于是,一年夏天,我突发奇想,关闭现代便捷的通讯,远离喧嚣的城市,只身来到深山,试图做一回“武陵捕渔人”。
深山里的小村庄,只有百来户人家,留守的不过几十个老人。朋友的母亲给我递上一杯茶,没有茶叶,握在手里凉冰冰的,黄澄澄的。客人登门不是现泡茶,莫非是山里人的待客之道?疑惑中,一股清爽的草药香飘进鼻腔,随着呼吸道沁入肺腑。是草药,我作出了判断。杯子举到嘴边,用唇轻轻抿了一下,有股淡淡的药味,还有一点点苦。朋友母亲见状,笑着对我说:“这是六月霜茶,清凉败毒的,小孩子喝了夏天都不长痱子,是我们山里人夏天的清凉饮料。”我点点头,捧起茶杯一饮而尽。
烈日下正午的村庄,空气中弥漫着六月霜的草香气。有老人驻守的家门前,地上都摊晒着六月霜。刚摘来的青枝,枝叶蓬松,显露出深林原始的面貌,当它们与太阳友好地会面后,逐渐褪去那份张扬,藏起浓缩的精华,成为大山献给山里人一夏的馈赠。
我去采过六月霜,哦不,我又说采了。老人们常常纠正我,是割不是采。哎,城里人总是文绉绉的。
朋友的母亲带我去割六月霜,彼时她已经年过八旬,走在“S”形的山间小道上仍健步如飞,我时而要小跑几步才能赶上她。幸好六月霜长在山坡林边,不用爬高山,但是长在灌木丛中,蛇虫也让人生畏。
山里人对于大山的了解,如同对自己的家人一样。哪里有解渴的一孔水,哪里有充饥的一棵野果树,都了如指掌。当然,这里的六月霜最茂盛。
六月霜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今年割了来年又长,生生不息。植株茎秆上遍布白色绒毛,上端开满了淡粉色的小花,远望近观,都如六月天降浓霜,一片雪白。
六月霜的茎细硬密集,只见老人左手扒开荆棘,精准地捋出一把六月霜,右手举起镰刀,这样一拉,一把六月霜顺势倒在了脚边。灌木丛中,老人用她干树枝般的双臂,左右开弓劈开一条路,我跟在后面捡拾,手背还是免不了被荆棘划出几道血痕。
太阳刚从山坳里露出来,我们各提一笋袋(挖笋时装笋用的)六月霜满载而归。被露水湿透的裤管牵绊着双腿,我笑自己像瘸子一样。老人家却卷起了裤腿,比我走得轻松爽气。
劳作后,喝一大杯隔夜的六月霜,清凉沁心,通体舒畅。
见过介绍六月霜茶的制法:取干六月霜一小枝,将其折成小段,放入清水中煮开,待凉后即可饮用。
在热情淳朴的山里人家做客,是大把的干六月霜用山泉水煮茶,大钵头里凉着的,散发着森林天然的芳香,听得见小溪潺潺泉水叮咚树叶沙沙,尝到的尽是浓浓的乡情味道。
每到三伏天,我一定会打开包裹,像山里人一样把六月霜晒晒。见到保存完好的六月霜,我仿佛重见老人家那双爬满皱纹而坚实硬朗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