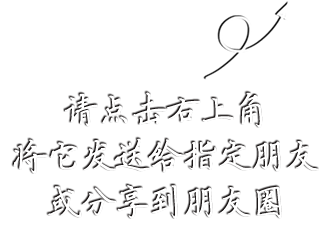□萧余
里畈的船、山区的钢丝车、沙地的脚踏车(自行车),是过去农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工具。脚踏车和沙地人就像螺栓和螺母一样,紧紧拧在一起。
夕阳西下,在麻田,或稻田,或棉田劳作的人们抬头一看,立即欢呼:收工回家啰!于是纷纷跑到沟边、路边、田边扶起脚踏车,有的带着女人,有的驮着羊草或猪草,有的轻松单行……披着一身晚霞,一路铃声,一路笑声,十余辆脚踏车滑过一道道碧翠麻墙、穿过一片片绿茵稻海、飞过一块块青咖的棉田,形成一道移动的风景,向自己的“稻草窠”奔去。脚踏车的一串铃声,人们的一串笑声,给寂寞枯燥的沙地带来难得的活力,给艰难困苦的沙地人带来难得的欢乐。
沙地平坦辽远,脚踏车满足了稻棉麻轮作生产的劳作需求和沙地人的出行需求。即便在艰难窘迫的日子里,沙地人勒紧裤带也要拥有一辆脚踏车。在沙地,不少人家有脚踏车,且几乎都是28英寸重磅脚踏车。许多人会骑脚踏车,且几乎个个身手不凡:双抢时,两麻袋300多斤重湿谷,呈“八”字形架在后座两边,脚踏车飞驰在机耕路上奔去晒场晾晒;剥络麻,两捆一个半人高的湿麻秆,呈“人”字形架在后座上,脚踏车在田埂上飞快地向家移动;摘棉花,塞满潮棉花有半人多高的白布袋横缚在后座上,脚踏车穿畈越桥地赶着去晒场晾晒;3只圆鼓鼓甏里装了200来斤重的萝卜干,呈“品”字形扎在后座上,走街串巷一路骑行一路叫卖,少则骑行五六十里,多则要骑行上百里地;施粪肥,后座上横根扁担挂上两只装满粪肥、浮着南瓜叶的粪桶,为防止转弯车侧粪“晃出”,为防止车震动粪“溅出”,小心翼翼地缓慢骑行;运化肥、驮番薯、拖甘蔗、拉稻草……沙地农活都离不开脚踏车。就连头刚探出车高的小囡,割完羊草猪草后,将后座垒得又高又满,双手扶把手,右脚穿过三角架,弯斜着骑着脚踏车回家。远远望去,只见一座“草山”在慢慢移动。
“贼贼细”的田塍路,沙地人骑行自如;遇到小田缺,沙地人一抬龙头轻松越过;走亲戚、上集镇,大孩子坐车横档,女人抱着小的坐后座,后座两边挂着地里收获的土货,男人骑着“一拖三+”的脚踏车春风得意……平展的路成就了脚踏车在沙地重要地位,脚踏车成就了沙地人绝妙的车技。
在计划经济年代,沙地人买辆脚踏车不容易,在嘴巴里抠、在衣着上省,七拼八凑攒足一百五六十元钞票,除了供销社每年分给大队一两辆脚踏车外,其余得“求爹爹拜娘娘”地托关系搞“车票”,才能买到“白市”脚踏车。没有关系的人,只有“咬个痛指头”,买高出“白市价”许多的“议价车”。实在没有办法的,就想方设法买辆旧脚踏车……唉,没有办法啊,脚踏车在沙地实在重要!1982年,在头蓬的表兄,坐班车到城厢镇,走五六里地到萧山火车站,再坐火车到临平,花了大半天时间,饿着肚子绕了个大圈子,就是为了到我处买辆永久51型重磅脚踏车。
沙地人在向往美好生活的征途中不断前行,但时间难以擦去沙地人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