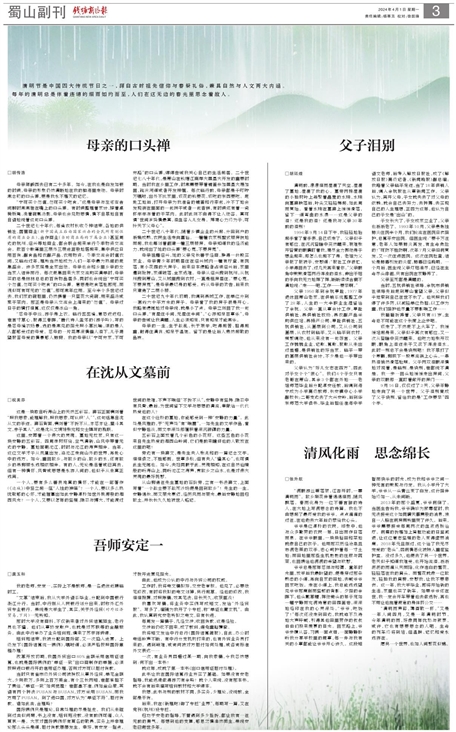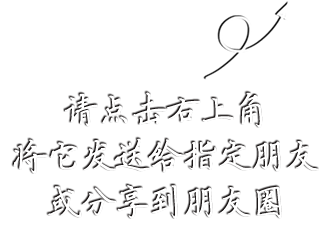□胡廷煌
清明前,濛濛细雨湿漉了天空、湿漉了墓地、湿漉了我的心。墓旁两株湿漉的小柏树叶上凝聚着晶莹的水珠,水珠向墓碑跌落后,叶尖又轻轻弹起,如此周而复始。看着水珠在墓碑上缓缓滑落,留下一道弯曲的水渍……这是父亲的泪?还是我的泪?还是我与父亲30年前的泪别?
1994年9月14日下午,我轻轻地抬起手看了看手表,自己该走了。父亲似乎有感应,在沉沉昏睡中突然醒来,艰难张开昏黄的眼睛盯着我,竭尽全力挪动身子想坐起来,却怎么也起不了身。老姐为父亲掖了掖被子,安慰道:“报社工作很忙,小弟得回去了,过几天再来看你。”父亲眼角中默默滑落两行浑浊的泪水,伸出干枯的手向我无力地挥了挥,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地说:“走——吧,工作——要紧啊。”
父亲1950年到余杭亭趾,1977年退休回萧山老家,在供销系统整整工作了28年,人生的一大半职业生涯留给了余杭。父亲一直从事会计工作,亭趾供销社、县供销社牧场、县农副产品采购供应站、县特产公司、亭趾供销社、五杭供销社,从基层到公司,又从公司到基层,从农村到临平,又从临平到农村,频繁调动,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父亲工作兢兢业业,记账、算账、报账从未出过差错,是供销社的好当家。临平一带的基层供销社会计,不少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父亲认为“好儿女志在四方”,因此对子女个个“狠心”。我们4个子女只有老哥在萧山,其余3个都在外地——老姐师范毕业后分配淳安任教,后调到海宁成为小学高级教师、长安镇中心小学副校长;二哥支边去了大兴安岭,后到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毕业后担任淮海中学语文老师,后考入解放日报社,成了《解放日报》高级记者、《新闻晚报》副总编;我踏着父亲临平足迹,当了18年供销人后,调入余杭报社从事新闻工作。父亲认为,离开父母,子女就失去了对父母的依赖,就会自己去努力、去拼搏、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自己的子女是“出山”的。
子女长大了,子女成家立业了,父亲也渐渐老了。1993年10月,父亲患急性肺炎住院半个月,我们轮流在医院日夜陪护,总算平安出院。但医生说:“要千万注意,老年人如果肺炎再发,有生命危险的!”可防不胜防啊,次年7月父亲旧病复发,又一次住进医院。这次住院检查,结论是肺癌引发的炎症,肺癌已经晚期。一个月后,医生说父亲灯枯油尽,已经在生命尽头徘徊,只有出院在家静养了。
父亲至死都是清醒的。
当时,五杭供销社领导、余杭市供销社领导先后赶到萧山看望父亲,父亲似乎觉察到自己在世不长了。他关照我们停了许多药,以减轻单位负担;以工作为重,我们陪护他尽量不要影响工作……
我暗暗祈祷着,父亲只有81岁,生命总不可能在这个长度上止步吧。
该走了,不然赶不上火车了。我缓缓站起身来,父亲似乎再次有感应,又一次从昏睡中突然醒来。他吃力地张开双眼,眼角上泪迹未干又滚下浑浊泪水。此时一别总不会是诀别吧?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脚底下一股寒流袭上心头,一串热泪悄然滑落脸颊。父子两双泪眼深情地对视着,是临别、是诀别,谁都说不清楚。我一步一回头地缓缓走出房间,父亲的双眼却一直盯着敞开的房门……
9月16日,仅仅过了2天,父亲平静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父子泪别竟成了父子诀别,留给我的是“工作要紧”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