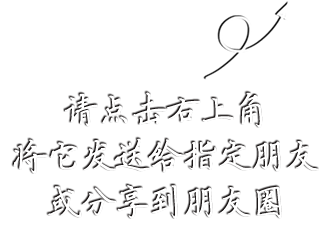□董萍
人的一生,总是匆忙地行走在路上。一路的憧憬,一路的相遇,一路的风景,一路的欢愉,便是一生的精彩。
挑一段最好的时光,重拾独行的自由,追忆那逝去的青春,回味曾经的美好,背起双肩包,行囊轻轻,信心满满,把杭州记忆暂时清零,再续一场酣畅淋漓的旅行。
对于我这个喜欢独行的人来说,选择小渔村的渔家住下,是最合适不过了。
但凡靠海吃海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每日晨光未露踏浪出海,迎接喷薄而出的第一缕阳光,任凭海风狂烈,颠簸的小型张网渔船,总会满载而归。收获的喜悦,成就了他们大海般宽广的胸怀,对待外地游客,如对自家人一般亲近热情。
置身出门见海的渔村,人被海洋的气息裹挟,晚间枕着涛声入眠,晨间被橙红的朝阳催醒,睡眼惺忪地深呼吸,把风带来的海水味贪婪地吸进体内,唯恐错失了此刻大海难得的赐予。
去海边度假,心之向往。迎着朝阳,漫步海滩,看身影由长渐渐缩短;海风阵阵,海浪逐逐,奏响一曲优美的大海乐章,清净了脑中繁杂,清空了人的心灵,胸怀从此如海洋宽广。
旅游于我的意义,一定是唯美食不可或缺的沉浸式体验。独自出游,所到之处皆是好吃的美食。
蔡澜在《有情才有调》一文中写道:“做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是很过瘾的,这自己知道,旁人不会了解。”深以为然。记得有作家如是说汪曾祺先生,大家一起去开会,到一地,人家都跑去书店看书,只有他跑去菜场里面。可见老先生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去海边,吹海风深呼吸,听涛声看朝阳,踏浪闲等渔船归。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惬意舒适回来了。
一叶小舟从晨曦中显现,在霞光里渐渐清晰起来,目之所及,原来是一艘小船,渔家自备捕鱼的网船,船老大一人掌舵。船停靠在一条十余米长,供小船停靠的简易船埠,锚定在旁边。我走近,探身俯瞰船肚,见几只不大的水桶,里面用海水养着不同种类的海鱼,只认得一条不停张嘴呼吸的鱼,便向船家买回。形似锅盖(如果没尾巴,像多宝鱼),扁扁的,尾巴如筷子细长,俗称“锅盖鱼”,学名叫“鳐鱼”。虽说从小生活在沿海城市,但吃到的锅盖鱼要么是冰冻的,要么是渔民腌制过的鱼干,从未见过鲜活的锅盖鱼,很是新奇。渔民骄傲地科普,这鱼生活在海洋深处,野生的难得捕到,岸上气压大,不一会儿就会死。美味不可多得,赶紧带回渔家,女主人直赞运气好,帮助剖肚清洗,不加任何调料清蒸。
逛菜场寻鲜活鲜货,也是旅游的乐趣。一次偶然见得,在鱼摊众一隅,有一只不起眼的小盆,里面卧着几头海参,我以为是干货水发的,用手轻触,却会蠕动。活的海参!我发出一声惊叹。一个念头起,吃海参刺身,于是买了两个活生生的野生海参带回渔家。
女主人说,活的海参千万不能沾油,沾了油海参会化成水的。你会做吗?
“我不用油,吃生的。”我说。动手开膛剖肚,抽出肠子,全程用海水清洗干净,切薄片码盘,一叠酱油挤一条青芥末蘸食,大快朵颐,一会儿就光盘。
吃了各种渤海湾鲜活的海鲜,韭菜花酱是最能治愈人心的调味料之一。
带了女主人腌制的韭菜花酱回杭,一盘韭菜花酱凉拌豆腐,南北千里,却近得零距离。绿白相间,咸鲜调和,相得益彰。成就美味,原来很简单。
渔家自晒的淡开洋,十分干,一般难买到,头水的海带,也不是冒充货。夏日,一盘开洋蒜泥凉拌海带,金色的虾米,弯弯如钩,钓起了海洋的翠绿脆爽,激荡起浪花朵朵,送来舌尖的跳跃满足。
都说,美食能治愈人心,有点空洞,让人抓不到实在。说直白一点,自己喜欢美食,动手做一道对胃口的菜肴小点,无论价值,治愈率百分百。
我一向认为,欣赏食物,会吃不会做,只能了解一半。真正懂得吃的人,一定要体验厨师的辛勤和心机,才能领略到吃的真髓。不是我说的,是蔡澜说的。